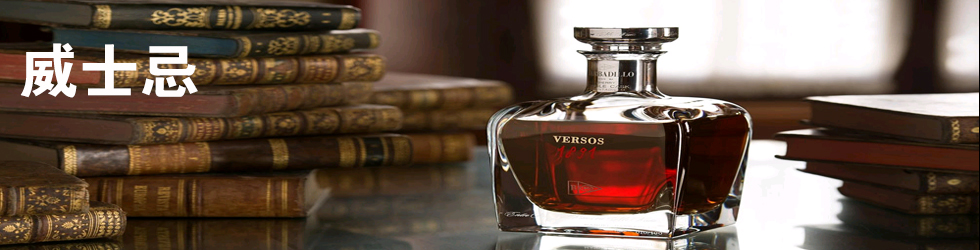在很多人心目中,凯尔特人即为爱尔兰民族,这也许是年爱尔兰共和国独立给公众造成的印象。事实上,凯尔特人原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中欧、西欧的一些部落集团,经过漫长迁徒来到英伦,其后代今散落于爱尔兰、威尔士、苏格兰北部与西部山地各处。凯尔特人包括爱尔兰人、苏格兰高地人、威尔士人及康尼士人,他们大多操双语——英语和本族语(盖尔语或凯尔特语),但往往不同地区的同族后辈,语言上会有较显著的差异。除了文字或文物研究可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族源关系,最直接的方式是倾听他们用小竖琴和风笛奏出的音乐,那种古老的、源远流长的音乐,已成为连接不同地域凯尔特民族的文化纽带。
可惜,近代有关凯尔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极不详尽;几乎在整个唱片工业体制趋向成熟完善之后,凯尔特音乐才受到重视。男高音歌唱家约翰·麦克康马克是本世纪初惟一一位较出名的凯尔特裔早期录音明星。麦克康马克早年在米兰学习声乐,年在伦敦首次录音并开始定期在伦敦修道院花园公演,在曲目选择上,麦克康马克渐渐加入改编自爱尔兰民间音乐的作品:《游吟男孩》、《爱尔兰移民》、《你若阳光般微笑》,这些作品在他的演唱下,成为广闻于世界的爱尔兰民歌。麦克康马克录有数百张专辑唱片,总销量在二千万张以上。他将爱尔兰民间音乐有效地与古典音乐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形式,启发和激励了不少凯尔特后继者。迪莉亚·墨菲就是其中一位。
迪莉亚·墨菲沿着麦克康马克的方向继续拓展,她所演唱的由约翰·弗兰西斯·沃勒创作的歌曲《飞转的轮子》,其轻妙的爱尔兰乡音与盖尔古腔,辅以竖琴的伴奏,很快成为本世纪上半叶爱尔兰音乐的代表风格。墨菲不单限于爱尔兰民乐改编,通过一系列歌曲如《如果我是只黑鸟》、《厨艺歌》、《再见麦克,再见派特》、《劳拉·克莱那》等,墨菲在民族音乐中巧妙溶入美国百老汇与爵士乐元素。二战后墨菲进行一些歌曲翻译工作,将凯尔特语转译成意大利语,进而将优秀的爱尔兰民歌推向整个欧洲。
然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,闻名于世的凯尔特风味作品,大都出自于那些远离凯尔特文化中心的、散居于美洲大陆的凯尔特移民后代,如歌手丹尼斯·戴,竖琴手艾米丽·米切尔,多种乐器演奏家凯特·史密斯、罗伯持·怀特。当然,出入于此的也不乏古典乐界的名流,如罗伯特·肖合唱团、阿瑟·福莱德率领的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、吉他名家约翰·威廉姆斯、长笛演奏家詹姆斯·高威;居住在英国本土的约翰·泰夫纳,也曾以古典手法出版过基于凯尔特传统的现代交响乐《凯尔特安魂曲》。这些艺术家利用改编凯尔特民间音乐,创造出一些“别有风味”的作品,这些作品往往会令人理解为古典音乐的通俗表现。论到真正扎根于凯尔特文化的艺人,依然要看那些来自英伦三岛的当地居民。
高地酋长乐团成立于60年代。乐团成立时,其大部分成员都已是都柏林市最好的民乐艺术家。他们以古老的乐器演奏传统乐曲,这些乐器大致包括:肘臂风笛、提琴、木笛、锡哨、双风箱手风琴、竖琴和羊皮鼓,这也是爱尔兰土地上流传最普遍的乐器。尤为可贵的是,他们再现了一种非常古老的凯尔特民间乐器——爱尔兰扬琴(timpan)的魅力,并运用双簧管的清亮音色与之进行合奏。这种古老的编排,使他们演奏的传统乐曲丝毫没有牺牲在现代口味上,而是获得了本色的再生。高地族长乐团的成立,最早是受到年轻创作者西恩·奥·瑞阿达的启发,瑞阿达曾试图改编民歌为协奏曲,并成立一个叫CeoltoiriCualann的团体进行实验。后来该团团员、提琴手马丁·费,伙同派蒂·莫龙尼、西思·波茨、迈克尔·脱布里地一起,成为高地酋长的原始团员。后,又有西恩·肯尼、德里克·贝尔等成员加入。无论专辑出版还是现场演出,高地族长都无须担心凯尔特一盖尔神韵的遗失,同时却又能打破以往民间传统乐队在演奏上的框架约束。他们在乐曲中段改变节拍,增加变化,可以从里尔舞曲(reel)的单四拍子,转换成基格舞曲(jig)的复二拍子或三拍子,再变成波尔卡(Polka)或舒缓的慢舞(slowair),这些尝试引发了一系列民间乐团的变革。在高地族长乐团的25张专辑中,演奏曲目主要以传统乐曲为主,这些作品是了解爱尔兰凯尔特文化的重要资料;另一部分作品,系与不同风格不同国籍的摇滚、民谣艺术家合作,从音乐章节、和声方式、节奏拍子诸方面进行实验,古远如17、18世纪的古琴曲,可以与20世纪的布鲁斯音乐结合,这给远离凯尔特文化中心的美国音乐家以许多新的乐思。其中,专辑《高地族人》之一、五、七,《早一点热早餐》,《爱尔兰的心跳》,电影配乐作品《巴里·林敦》,成为高地族人最出色作品集。
在坚持以传统乐器演奏原汁原味民乐的乐团中,还有以提琴手艾里·贝思领衔的爱尔兰—苏格兰乐队“海湾之子”,苏格兰“战场乐队”,爱尔兰“斯托克顿的翅膀”乐队,以及格拉玛丽乐队。虽然他们出现的年代先后不等,但在立足传统方式保存凯尔特音乐这一点上是相同的,所以他们共同组成了凯尔特音乐的中坚力量。当然,在演唱者方面,西莫斯·恩尼斯与苏格兰乐团凯坡赛里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凯坡赛里的专辑《血是热的》、《与爱人同行》,都属于极传统的盖尔语佳作。
50年代大西洋彼岸发生的民歌复兴运动,也逐渐波及到英伦三岛,使众多年轻人醉心于民歌之上的新的创造。来自于同一音乐世家的汤姆·克兰西、派蒂和雷姆,成为最早去美国学习考察唱片体制的爱尔兰青年。在唱片公司“民谣之路”(Folkways)和“伊莱克托”(Elektra)帮助录一些爱尔兰民歌后不久,派蒂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——取名为“传统”(Tradition)。年,“传统”在英国发行乔什·怀特与黑人民谣女歌手奥黛特的小唱片。克兰西的另两个兄弟,则着手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进行民歌搜集工作,在遇到北爱尔兰乐手汤米·麦克姆之后,三人组成了克兰西兄弟乐队。克兰西兄弟演唱的民歌,如《一壶五味酒》、《利物浦的渣》,在大西洋两岸普遍受到了欢迎。而乐队成员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唱片,成绩也十分出色。在克兰西兄弟之后,又出现了都柏林人,这支乐队起先由乡村教师朗尼·朱组建,于年以朗尼·朱小组的名义在都柏林酒吧中演唱,名声传遍全爱尔兰及英国;中途又有前“绘图员”乐队成员约翰·谢汉、鲍勃·林奇加入,一系列的现场表演特别是在伦敦塞梭·萧宫殿的表演,宣告了凯尔特民谣的被广泛认同。30年后的今日,“都柏林人”已被视为爱尔兰民族艺术的象征性团体。
在以上乐队的影响下,苏格兰出现了伊安·麦卡尔曼民歌小组,后更名为麦卡尔曼们;北爱尔兰出现了“他们”乐队,爱兰出现军校生乐队。对于北爱尔兰地区,宗教、种族问题没有像南爱尔兰那样因为独立而获得了解决,历史的变迁反而使其更加尖锐。年,冲突演变为武力对抗,艺术家们十分